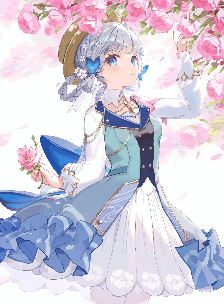第1章 安伶
雨是半夜下起来的。
般若支着下巴坐在典当行的二楼,指尖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楠木算盘。珠子碰撞的声响混着雨声,像谁在暗处数着不清不楚的烂账。
楼下当值的伙计早溜去睡了,横竖这年头肯半夜冒雨来典当的,不是亡命徒就是冤死鬼——而这两种人的生意,向来只由少爷亲自接手。
“啧,晦气。”他摘下金丝边小圆墨镜,揉了揉眉心。今晚的账目格外烦人,算来算去,数字总对不上,仿佛有人偷偷从他钱箱里摸走了一把银票。这种没由来的亏空感让他牙根发痒,索性把算盘一推就要休息,谁知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一声闷响。
般若的手指一顿——
他思躇良久,终于起身踱到窗边,掀开半角帘子往下瞧。昏光里蜷着个粉色的小东西,雨水把她的头发糊成狼狈的绸缎,昂贵的洋裙下露出一截猫尾巴,正随着呼吸微弱地起伏。
看来,今夜的生意可以是稳赚不赔的死当。
————
晨光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,在木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安伶——或者说,此刻化名为安伶的少女,正安静地坐在角落,指尖轻轻着搪瓷杯的鎏金边缘。杯中的黑咖啡早己凉透,表面凝结着一层薄薄的油脂,但她似乎并不在意。
她看起来和云莱城里任何一个年轻姑娘没什么两样:棕发扎成两条乖巧的麻花辫,浅棕色瞳孔清澈得能映出整座城市的倒影。没人会想到,这副人畜无害的娇小皮囊下,藏着一张连凶悍的猎人都要退避三舍的躯体。
“安伶”——这个随手取的名字,从昨天开始成了她的新身份。
《云莱晚报》的面试比她预想的还要顺利。
“你确定能胜任?”主编推了推金丝眼镜,镜片后的目光像把解剖刀。这位戴着鹿角装饰的中年男子是云莱典型的半妖——人类外表下流淌着部分精怪血脉,这在人妖共生的云莱再常见不过,“我们不要温室里的花朵。”
安伶从帆布包里取出一叠泛黄的稿纸。纸张边缘己经起毛,沾着可疑的暗红色污渍。这是三年前她潜入故葬黑沼时写的任务报告——昨日被她修改成纪实,字里行间还弥漫着沼泽特有的腐臭味。
“比这更脏的地方我都蹚过。”她声音很轻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,“如果贵报想要真正的猛料,我想不出还有谁比我更合适。”
主编的眉头在读到“尸体像腐烂的莲藕般漂浮在沼气里”时跳了跳。他抬头时,眼神己经变了。
“不要命了?”
“要命的人,”她将一缕碎发别到耳后,“在故葬活不过三天。”
就这样,她拿到了记者证。墨绿色的封皮烫着金边,摸起来像块冰冷的墓碑。
而从踏入云莱那刻起,她就必须斩断所有明面上的与家族中人的联系。
——至少看起来是这样。
卡琳家的人最擅长蛰伏。他们像毒蘑菇的菌丝,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城市的砖缝。此刻她的“家人们”可能正扮作古董商、黄包车夫,或是蹲在街角擦皮鞋的瘸子,在暗处编织着一张无形的网。
唯一光明正大跟着她的,只有黎珐。
那只灰白相间的猫正蜷在她膝头打盹,尾巴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打着她的手腕。在旁人眼里,这不过是只普通的家猫。谁能想到它锋利的爪尖能割开成年男人的喉管?
安伶端起咖啡抿了一口。劣质咖啡豆的焦苦在舌尖蔓延,她却连睫毛都没颤一下。
她来云莱,可不是为了写什么劳什子新闻。
——多昂·登·卡琳。
这个名字像根生锈的铁钉,狠狠楔进她的记忆里。
卡琳家规第一条:背叛者死。
那个杂碎居然敢出卖食月森林的情报。那片终年笼罩在毒雾中的原始森林,是卡琳家最后的庇护所。当年暴乱时,他们被驱逐到那片连飞鸟都会融化成血水的死亡之地,硬生生杀出一条活路。
云莱人只知道“故葬”是建在万山沼泽上的流放地,却不知道那些嶙峋的山峰间早己立起摩天大楼。西大家族掌控着这座罪恶之都的命脉,而卡琳家,靠的就是让众人夜不能寐的追猎能力。
自由不等于背叛。
多昂犯下的罪孽,必须用鲜血来偿清。
银制的咖啡勺突然在杯沿敲出清脆的声响。
云莱还在用那些老掉牙的银元铜板,而故葬的“弗琅”是整块紫水晶雕琢的硬币,一枚就抵得上这里二十块大洋。那些晶莹剔透的货币在阳光下会折射出妖异的紫光,像极了故葬人骨子里的疯狂。
她唇角勾起一抹猫儿似的笑——
好戏,即将开场。